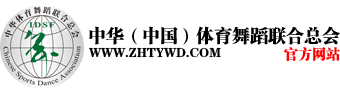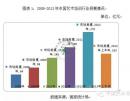“当代芭蕾舞坛,如果NDT说自己排第二,没有舞团敢说自己排第一。”舞蹈家黄豆豆是荷兰舞蹈剧场(简称NDT)的超级粉,在接受采访时,他曾如此形容自己眼里的NDT。这样的艺术地位,和NDT前艺术总监依利·基利安脱不开关联。1975年,年仅28岁的基利安出任NDT艺术总监,两年后即凭一部《小交响曲》将舞团推上世界舞坛。同年,他开创了NDT2团,独创了依年龄划分舞团的全新模式,亦凭大刀阔斧的改革将舞团推上当代芭蕾之巅。以至后来,舞蹈界将1977年当作当代芭蕾的起始,基利安亦因此成为舞蹈史上的“丰碑式”人物。
11月14日至15日,NDT1团将携《动·静》登临上海大剧院,基利安旧作虽不上演,但他之于NDT就像“符号”甚或“图腾”般的存在,要了解NDT以及当代芭蕾的发展,基利安绕不过去。
“世界公民”的学舞之路
现年67岁的基利安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,9岁入读布拉格国家剧院芭蕾舞学校,15岁进入布拉格音乐学院,曾先后接受古典芭蕾、民族舞蹈训练。布拉格音乐学院也是东欧当时唯一一所会上玛莎·格莱厄姆现代舞技术课程的学校,因而在功底上,基利安有俄罗斯的古典芭蕾打底,又受益于美国现代舞,在身体的中段(躯干)得到全面训练,其舞蹈感染力并不止于指尖和脚尖,而是从内向外全身心发散。
基利安很早便开始帮小伙伴们排舞。十二三岁时,他常把自己关在房里,放音乐,即兴创作,直至累瘫在地。“我想成为努里耶夫,但当我意识到我不可能成为努里耶夫时,我发现通过别人的肢体表达,远比用自己的效果更好,也更容易。”
英国文化委员会部长Jennie Lee是基利安艺术之路上的第一个“贵人”。当时,Jennie Lee至布拉格为英国雕塑家Henry Moore办展,看到了基利安排的第一支舞,“我能看出来,你的才能不仅体现在肢体上,也在你的头脑中。”因为这句话,基利安后来一直感激她,他也因此获得英国皇家芭蕾学校修习一年的奖学金,“这打开了我未来的道路。”
1967年,20岁的基利安只身来到英国。那时的英国皇家芭蕾舞团正处巅峰状态,阿什顿和麦克米伦的“戏剧芭蕾”创作如日中天。这时的英国文化也正处在各种艺术思潮的激烈碰撞中,“你能想象么?在那里一切都可能发生。那里有披头士、滚石、猴子、大门乐队。那里有努里耶夫和玛戈·芳婷。我第一次见到了玛莎·格莱厄姆。当代艺术学院那年刚刚成立。我去看了每一场音乐会,每一场展览,所有我能看到的。”
基利安显然对编舞更有兴趣。当时,他甚至问英国皇家芭蕾学校校长德·瓦鲁娃可以去哪学编舞,瓦鲁娃回说,“唯一的方法就是多看经典。”因为英皇学生的身份,基利安有机会出入英国皇家歌剧院看英皇的排练、演出,他疯狂“存知识”,对古典芭蕾的传统熟稔于心。
1968年,德国斯图加特芭蕾艺术总监约翰·克兰科访问伦敦,一眼相中基利安,“我想在斯图加特跟你签约,来这吧,这里一直都很明媚。”但当时的捷克正经历“布拉格之春”运动,又遭苏联及华约成员国武装入侵,基利安无法获得签证,干脆跳上了去德国的火车。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,基利安持有的都是无国籍护照,护照呈灰色,页脚有黑色条纹,“就像这个人已经死了。”拿着这本护照,基利安成了NDT艺术总监,他甚至曾以持无国籍护照的移民和“叛徒”的身份,带团参加了1980年的“布拉格之春”音乐节,随时有被逮捕的可能。谈及归属感缺失对自己的影响,基利安说,“我是四海为家的。自始至终,我都觉得自己是一个世界公民。”
克兰科一手将籍籍无名的斯图加特芭蕾舞团推至现代芭蕾之巅,他亦鼓励舞者独立创作,成立青年编舞工作坊,为其提供舞者和表演场地的协助。基利安、威廉·福赛斯、约翰·诺伊梅尔等一批当代芭蕾大师,都自此脱颖而出。1973年,基利安受NDT之邀创作,为其今后在NDT工作三十余年打下伏笔。也是这一年,克兰科突逝,对舞团打击甚大,基利安亦深陷悲伤。1974年,基利安创排了成名作《回归荒原》,向克兰科致敬,抒情芭蕾中雕塑般的质感,成为基利安步入“伟大”的开端。
当代芭蕾从他而起
NDT在世界当代芭蕾舞界的标杆地位,从1975年开始。这一年,基利安受邀出任NDT联席艺术总监,而他独立执掌NDT的1977年,则被业界公认为当代芭蕾的起始时间(现代芭蕾为1909年-1977年,当代芭蕾为1977年至今)。在创作风格上,基利安先后受到约翰·克兰科、汉斯·万·曼能、葛兰·泰特利、莫里斯·贝嘉等人的影响,“但如果往前回溯,所有现代编舞家都受到了玛莎·格莱厄姆和乔治·巴兰钦的浸润。”
1978年,基利安在美国查尔斯顿艺术节带团出演《小交响曲》,将NDT推上世界舞坛;1980年代初,基利安进入原住民仪式和文化的探索,代表作有《足蹈大地》;继而,基利安走向《顽童惊梦》等较为剧场化的芭蕾,却受到荷兰舞蹈界抨击,使他开始思考舞蹈本质及自我的局限;1988年,基利安借“黑白舞蹈”系列重获新生,接连推出《游戏不再》、《落凡天使》等登峰造极之作;1993年,基利安又于《在未知的地方》中达到另一个巅峰状态,日本佛教的智慧、无欲、无惧,日本建筑的原始和天然,让基利安的艺术走向了质朴与简约。
“如果说看古典芭蕾的眼泪是从眼睛里流出来的,看巴兰钦舞蹈的眼泪是从心里流出来的,那么观看荷兰舞蹈剧场的演出,人们的眼泪则是从每一个细胞里流出来的。”2010年NDT2团来华演出时舞评人欧建平随口一说的这句话,几乎成了NDT最好的“广告语”。
在欧建平的印象里,基利安的作品并不讲故事,也并没有揪心的男女之情,以及因此而来的悲剧感。他单靠舞者(舞蹈本体)本身,便能让观众的每一寸肌肉和细胞跟着激动。舞者在他的引导下,肢体开发充分——集中于身体四肢的芭蕾舞,和集中于身体躯干的现代舞,都能在他的作品里得到全身心调动。“他最了不起的地方在于将芭蕾舞和现代舞完全打通,舞者的气息在全身流动,不堵塞,人整个是活起来的。”
基利安的编舞风格也得益于此。他秉持的“折中主义”和“中庸之道”,既不前卫,也不激进,而是将畅若流水的古典芭蕾与抑扬顿挫的现代舞结合,具有强烈形式感的同时,又在内涵深处燃烧着对人类命运的关注,并随时会迸发出浓郁的幽默感。和基利安同时代的福赛斯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,欧建平将之戏称为“拆骨”式编舞,“恨不得把人的胳膊、腿拆了,大卸八块”,极为考验舞者的身体条件;诺伊梅尔则因文学和戏剧功底而专注于戏剧芭蕾,十分擅长讲故事。
和很多思维缜密的理性编舞家不同的是,基利安很大一部分是靠直觉编舞,“但我也并不懂我的直觉。”他作品中的元素运用多寓意鲜明。比如“黑白舞蹈”系列中女性身穿的黑色晚礼服,男性手中的剑,黑色、金色等颜色各异的巨大绸布都有符号寓意;舞者的每一次上下场都样貌不一,均经过精心设计。此次即将来沪出演的《动·静》,某些元素上也继承了基利安的风格,舞蹈进行到一定程度,舞者便拖着巨大绸布走上舞台,布面铺满犹如尘埃的面粉,一二三一甩,所有的舞者便在尘埃里起舞。
基利安的贡献还在于,他开拓了舞者不论老少都能跳舞的观念,并为之创建了一种全新舞团结构——将NDT划分为三个团,每个团由三个年龄段的舞者组成:1团是主体,集中了最风华正茂的舞者;2团由年轻实习舞团转型而来,为舞者成熟进入1团提供过渡;3团则为资深舞者施展才华提供了表演空间,亦借舞者的历练表现人生的深刻。
1999年,基利安以驻团编导和艺术顾问的身份退居NDT二线。这一年,也被认为是当代芭蕾第一阶段的终结。被问及如何总结NDT的风格,基利安说,“NDT的舞蹈是非常诚实的,没有一点虚假掺杂其中。许多人只是把舞蹈当作一种消遣,我们致力于让人相信,舞蹈也是一种严肃的艺术,它与绘画、音乐、文学、雕塑和诗歌这些艺术门类同样重要。它们都是平等的。”
“很多人在编舞时喜欢玩一些舞蹈本体之外的东西。但很难有人在对身体的理解上,能达到基利安那样的高度。” 欧建平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