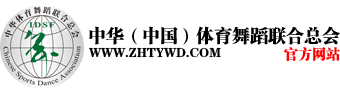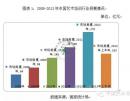侯莹不喜欢太美的东西。最早学民族舞时,她认为自己跳舞最大的障碍就是太美了,改跳现代舞以后,一直试图把“美”丢掉,呈现百分百的自己。在创作时,侯莹有意识地不想象任何画面,也不让音乐成为作品的限制,也就是说,肢体不会跟着音乐的情绪和结构运动,而是试图用肢体打破对音乐的一般运用。(图:第一个“涂”,是涂抹,第二个“图”,是涂鸦,就是“人跳到最后,满世界都是混乱的,面目全非,人也不见了,世界也不见了,都混在一起了”)
侯莹至今没有找到舞台上的最佳搭档,连与她合作多年、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沈伟都不算。2002-2008 年,作为沈伟舞蹈团的编舞和排练总监,她和沈伟合作紧密而默契,用侯莹自己的说法,虽不是情侣但却“很爱”。可是他们一旦一起跳舞就要吵架。因为沈伟始终不能完全摆脱编舞的身份,在台上“老是给Notes(提示)”,而她是完全投入的,觉得沈伟“太让人出戏”。现在的年轻舞者则不愿也不敢和侯莹同台,因为舞蹈太残酷了,一上台,谁跳得好谁跳得不好一目了然。有一次,她和自己创立的侯莹舞蹈剧场的舞者一起跳《介2012》,跳完后舞者们对她说:“以后有你就没有我们,有我们就没有你,我们是坚决不能在一起演出的。”
很多人在看过侯莹跳舞后,都评价说,无论有多少人在一起跳,总能一眼看到她。侯莹也知道自己非常耀眼:“我在舞台上那么自我,你怎么能看不到呢?我一直告诉我的舞者,跳舞的时候一定要跳自己的内心世界,把Notes 全部忘掉!”
作为国内最早一批由广东现代舞团培养的舞者,侯莹出众而又特立独行。她身体条件非常好,拥有最适合穿现代舞标志性的紧身舞蹈服的瘦削身材,可是非常不喜欢身体被束缚,认为“衣服紧绷,人也紧绷,选择什么样的衣服,就能跳出什么样的舞蹈”。所以她跳舞的时候要么穿长裙,要么穿宽松的裤子,平时出门则总穿男式睡裤,不过在那完全遮盖了身材的大裤子里面,你仍然能感觉到她的胯步在以一个舞者的方式运动。
侯莹还不喜欢太美的东西。因为最早在吉林省舞蹈学院学民族舞,她认为自己跳舞最大的障碍就是太美了,改跳现代舞以后,一直试图把“美”丢掉。她的编舞处女作《夜叉》就是一个名字和动作都不美的作品,“但百分百是我自己”。当时广东现代舞团的团长觉得她明明可以跳得很美,为什么要做那么丑陋的动作。开始侯莹听话去改,改来改去,最后编不下去了,只好回头凭感觉编,结果一鸣惊人,获得了第七届白俄罗斯国际现代舞大赛创作金奖。有观众说看这支舞的时候想吐,侯莹把它当作难得的赞扬。有时候,晚上睡觉前她跟自己说,闭上眼睛想想美好的东西吧,结果每每看到梵高给他的侄子画的,带有浮世绘风格的梅花:“那个蓝,它超出了正常人的想象力,是一种极美,不是正常人能想象的美。我不知道我的作品能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。”
在美国:幸福的舞者生活
2001 年,侯莹30 岁获得亚洲文化基金支持去到美国,美国现代舞对肢体的探索令她非常着迷。由于一心想把身上属于中国民族舞的“美”甩掉,她在现代舞大师莫斯·坎宁汉(Moss Cunningham)的舞团上了一年课。坎宁汉当时已经开始试验电脑编舞,编出的动作不符合逻辑,但非常具有启发性。
2002 年,侯莹加入了沈伟舞蹈团,连续四年在林肯中心登台,并于2004 年被《纽约时报》誉为年度卓越舞者。她刚入团时参演的作品,包括沈伟的名作《声希》与《春之祭》。他们两人配合完成的《声希》中的一段连体婴儿舞堪称经典,今年沈伟率团来上海公演这部作品时,还想邀侯莹再次登台。
那时候,成立不久的舞团经营十分困难,沈伟希望每个月能给舞者一千美元,实际上只能负担四百,每个舞者都要打两份工才能在纽约生活。作为排练总监,又是沈伟的“活舞谱”,侯莹每个月能拿一千二百美元,但是因为一心要住在曼哈顿,这些钱也只够她交房租。加上亚洲文化基金给的费用和国内的积蓄,勉强可以不打零工,专心跳舞。
“在美国的时候是很幸福的,每天就是很好地排练,晚上去吃一顿,然后看演出,休息的时候就去美术馆。”纽约浓厚的艺术氛围令她兴奋,在展览中看过的毕加索、波拉克、罗斯科等都在观念上对她产生了影响。“当时就觉得,哎呀,我们怎么过得这么幸福啊,”侯莹说,“尽管美国的舞团之间都是互换劳动力,相互之间是不给钱的,可是作为舞者,只要待在舞团,有舞跳,也不用考虑别的。”后来,她开始希望更多地自己编舞,因为都是签约舞者,排练一个舞至少三个月,舞团密集的巡演计划令她很难在一个地方待上三个月,于是她决定自立门户。
《涂图》:跳到最后面目全非
从2009 年开始,侯莹逐渐把工作重心从美国移回中国。开始她两边各待半年,去年卖掉了广州的房子,在北京东北郊设了舞团训练场,几乎整年都待在国内了。“国内简直太有发展了,这才第一年,已经忙不过来了。”
1月10 日,侯莹舞蹈剧场的六位舞者将在艺海剧院演出复排的《涂图》,这也是她旅美归国后第二次带作品来上海公演。《涂图》最早亮相于2009 年的广东现代舞周,就是“人跳到最后,满世界都是混乱的,面目全非,人也不见了,世界也不见了,都混在一起了”。
今年,侯莹将它重新编创成70 分钟的版本,其中约60% 是舞者的即兴表演,而且去掉了第一版中舞台上的色彩和作为布景的球体。“过去的作品是我过去的世界观。我的世界是这样的,充满了色彩,很丰满、很炫,在那个时候很真实。现在我觉得我炫不起来了。当我去掉这些东西的时候,我才发现排一个纯纯的舞蹈,纯肢体的,有多么地难,因为没有任何附加的东西作载体。好像我走到这里走不下去了,本来可以用另一个东西转化一下或者代替一下,这次我坚持要把‘另一个东西’拿掉。所以这个作品,真正困难的是走不下去了之后的后半部分,排得我要疯了。”在创作时,侯莹有意识地不想象任何画面,也不让音乐成为作品的限制,也就是说,肢体不会跟着音乐的情绪和结构运动,而是试图用肢体打破对音乐的一般运用。
另一方面,她也将自己浸淫东西方舞蹈多年来,对舞蹈语言的思考融入了《涂图》之中:“舞蹈语言发展到今天,没有哪一种语言是你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见过的,只是看你怎么用它。没有什么前无古人、后无来者,但是用法不一样,这些东西就成了你的语言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