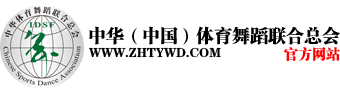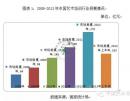昨日晨,中国舞蹈界大家资华筠作别了她87年的精彩人生。
资华筠首演的《飞天》、《孔雀舞》、《长虹颂》、《思乡曲》、《金梭与银梭》等,在整整一代人心中烙下美的印记,成为时代的标识、中国舞蹈艺术的经典之作。
告别舞台后,资华筠潜心学问,成为中国舞蹈界获得艺术、学术双项正高职称的专家第一人。
辞世前,这位传奇女性以坚忍的意志,与白血病抗争了整整十年。而就在这十年间,她的学术研究硕果累累,她的门下弟子桃李芬芳。
是舞者,是学者,更是大写的人。
“哎呀,哎呀,太遗憾了……”前天刚刚赶到台湾参加“第六届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艺术论坛”的中国舞蹈家协会驻会副主席冯双白接通电话后不停地感叹。他说:“我8日早晨6点结束工作,乘车去北京军区医院看望资先生,结果,走了一半,太堵了。如果我执意去医院,很可能误了飞机。而台湾论坛安排我是主持人,我不能不来。所以我一边想着没有资先生过不了的关,一边掉头到机场。结果,飞机晚点一个小时。把我气的!”
9日早晨7点10分,冯双白在台湾接到短信,资先生于半小时前去世了。
动荡的年代,不变的舞者之心
92岁、曾经担任过中央歌舞团副团长的孟于记得,在20世纪60年代,为工农兵服务是艺术工作者的宗旨。中央歌舞团几乎每年春节都组织节目深入基层演出。他们分成“工”、“农”、“兵”三个队,“农”队由孟于带队,资华筠是其中一员。在河北省平山县下盘松村,资华筠等年轻艺术家们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。孟于清晰地记得,资华筠一点都不娇气,其他女孩子身上还有点挑挑拣拣的小毛病,而资华筠一点都没有。
“文化大革命”时,孟于成了中央歌舞团第一个走资派。但孟于记得,在这个运动中,资华筠跟着喊口号不可避免,但年轻的资华筠在大运动的狂潮中,没有带头闹,更没有被裹挟进去。
那个年代,几乎所有艺术家都被耽误着。资华筠于1970年到1974年在坦克部队呆了四年,种稻田,修桥补路。
经过多年的压抑,20世纪80年代初,资华筠第一个带头和同行举办了三个舞蹈晚会,开了风气之先。1982年3月,终于有了机会,中央歌舞团组团到印度、尼泊尔访问演出,孟于是出访团的团长,资华筠担任这个团的艺术指导,整体负责节目的艺术质量。“虽然是‘艺术指导’,但是,不论哪个节目演员有伤病或其他意外,她都毫不犹豫地顶上去。”孟于回忆至此仍然感动不已。
奇迹般人生,舞者是大写的人
在台湾开会的田青听冯双白说到资华筠的去世,心生悲哀。因为资华筠和田青的一位叔叔算同辈人,因此,老被田青称呼“大姐”的资华筠就开玩笑说:“田青,你应该叫我阿姨!”
田青说:“资老师一生至少创造了两个奇迹:其一,是从舞者到学者的转型;其二,是与白血病常年斗争赢得时间培养年轻舞蹈理论家。”
资华筠出身名门,是著名学者资中筠的妹妹。那时,家里别的孩子都做学问,只有她爱上了舞蹈。家庭极力反对,但是她义无反顾。她曾经在电话里和老领导李凌的老伴汪里汶说:“家里人看不上我的职业,认为是四肢发达、头脑简单。我就立志不仅学好舞蹈,而且学好理论。”
田青说:“资老师的《荷花舞》等一系列作品引起轰动,成为中国民族舞蹈领域的领军人物,在表演上取得巨大成就。而中年,转型学理论做研究,她是从舞者到学者转型唯一成功的人。不说大家也知道,从事舞蹈、体育工作,在年轻的时候要把几乎所有精力都投进去,没有时间博览群书,因此大多从业者文化基础薄弱。但资老师却创造了一个奇迹,不仅成为学者,而且是这一领域最优秀的学者。”
现任文化部艺术科技司司长于平在1998年考取了资华筠的博士。他说:“大家都知道资先生是一位执著的担当者,自她从舞蹈表演艺术家艰辛转身为舞蹈学者之后,十分强调维护舞蹈的职业尊严和舞蹈评论的健康生态。她一直要求我们舞蹈批评要讲真话、明真相、析真理,这是她自己坚持的‘三真’。此外,她的特点一是敏捷,二是犀利,三是通透,四是友善。”
十多年前,资华筠得了白血病,要与疾病斗争,但是她要带学生,要改论文,因为身体原因,电脑不能用,她是一个字一个字用手改。因为重病在身,资华筠的日子是“数着过”的。正因为这样,她非常珍惜时间。汪里汶说:“她每天干什么,都要计划好。但是她乐观。”资华筠头发掉光了,她却对汪里汶说:“这样凉快,洗头方便。而且不少学生在国外,给我买各种头套,黄色的、黑色的,我变换着戴。”
这样的一个资华筠,却有两颗心。田青说:“一颗是‘热心’,一颗是‘直心’。”在田青眼里,资华筠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推动者之一。她在行内最有名的一句话套用了毛泽东那句“严重的问题是教育群众”,而说成“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干部”。田青说:“正因为这样,她并不讨官员们喜欢。她的‘直心’给人印象深刻,她不喜欢的官员,绝不虚伪,敢当面骂。所以,会有人不喜欢她,但是也怕她。”
冯双白说:“资先生为人光明磊落,一生求真知,认真理。她批评过很多人,但在为人这方面的坦荡,是我们的楷模。她不会一团和气,但是事隔几年,大家都承认,她批评得有道理。”
“热心人”、“直心人”资华筠在2014年岁末,借着即将飘零到北京的雪花做了“飞天”,她飞到了天上去,在天空中以深邃的理论与绚丽的舞姿,写出一个大大的“人”……
刹那芳华 三世青筠
2014年12月9日,北京寒冬的清晨,在医院辞别了资华筠先生。先生走得安详,学生心里却无法平静。先生从艺60周年的主题是“舞蹈点燃心灵”,我更觉得她是用自己的生命点燃了舞蹈。
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,先生一生的成就在网络搜索中俯拾可得。但一个人真正的学识和品格,却不是冰冷的网络所能够传递的。所以我是如此庆幸,能跟随先生左右,渡过博士寒窗,结下珍贵的师生缘分。那不仅仅是一段学业,更是一段难得的人生历练。
先生的很多学生都是我的师长,作为年轻后辈能够亲自跟随先生学习,自然是有点小小的得意。刚刚开始读博士的时候还颇有点惶恐,因为资老师的“严厉”和她的学问一样出名。后来看先生挺和颜悦色的,渐渐就放松了“警惕”,觉得自己硕士研究生已经毕业,又已任教多年,读博应该不会有什么困难。加上学校工作繁忙,学业上自然有所懈怠。资老师几次提醒我都没有太放在心上,于是先生专门找了一天时间和我闭门长谈,严词厉色地批评了我。那才真正见识了先生的严厉,自己那点小心思、小猫腻完全无所遁形,言辞之切让我深受震动。后来站在典礼台上接过毕业证书的那一刻,我的眼光穿过熙攘的人群,看到我的导师资华筠先生,静静地坐在观众席里,带着浅浅的微笑。韩愈的那一句千古名言闪过脑际:“师者,所以传道、授业、解惑者也。”终于发现对这句话的理解根本无法在字面的解释中得到,而是要穷尽时间去体验。就像先生,根本不是在“教”我,而是用她自己的生命在示范、引导着我。她的“严”不仅仅是对别人,更是对自己。所以她才会说“学生比天大”,所以她才会以坚忍的意志与白血病抗争了整整十年。而就在这十年间,她的学术研究硕果累累,她的门下弟子桃李芬芳。
先生的成名舞作中有《飞天》,著名美术大师叶浅予先生曾为她作画,并题曰“敦煌有飞天,华筠能舞之”。如今先生“飞天”而去,背影依然曼妙,向着那舞影翩跹的天国。
学生把先生的名字嵌入两句话中来送别先生,那也是先生一生的写照——“刹那芳华,三世青筠”。美好灿烂的年华不过弹指刹那间,青竹般坚贞的志节却会穷尽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三世!
《飞天》之后的华丽转身
上个世纪70年代末,中国文化界经过了十年禁锢后开始迎来春天,失去十年创作和演出机会的艺术家们也迎来了春天。记者就是在这个时候,第一次看到了资华筠表演的舞蹈《飞天》。那个时候,她就已经是家喻户晓的舞蹈家了。
后来,记者来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,这时资华筠也来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。记者了解到她当时是离开舞台后开始进行学术研究的,在此之前,她的所有学习都是通过舞蹈生活之外的自学完成。作为在舞台上已负盛名的舞蹈家,离开舞台后依然进行舞蹈学术的研究且有较大的成就者,确实比较少。这可能源于资华筠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,资华筠系中国著名金融学家、金融文化界的泰斗级人物资耀华之女,与其他两位姐妹并称“资家三姐妹”。其中,资中筠是著名学者,资华筠和资民筠都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从事学术研究工作。
1987年,中国艺术研究院邀请资华筠担任舞蹈研究所所长,在时年51岁的资华筠看来,这是生命旅程中的一次突然急转弯。她曾在就职讲话的开头说:“我是来学习的,不是来‘上任’的。只要肯学习,相信不会太晚。”自此开启一段学术生涯。资华筠知道,研究舞蹈不是表演舞蹈,没有学术成就等于零,于是,从基础理论开始,资华筠开始学术上新的征程,最终在舞蹈生态学等领域有了自己的学术成就。
资华筠对于学术研究有着很高的要求,二十多年来,她所著述的《舞艺·舞理》和《舞思》文集,以及与人合著的《中国舞蹈生态学导论》和《舞蹈生态学论丛》都是她的学术研究成果;而她带的研究生也成为当今舞蹈学术领域的顶梁柱;她发表的论文和散文都曾经对国内舞蹈界、文艺界乃至社会生活产生影响。
待人热情是资华筠的生活观念,生活中的资华筠朴实且直率,经常会仗义执言。作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,资华筠常常在人民大会堂参加活动。有一次参加完活动回家的路上,司机在一公厕前紧急停车,并解释说:“对不起,你们开会,我们没处上厕所。”资华筠听了非常内疚,她第一次了解到重大活动中,司机存在着上厕所难的问题。回来后她就写了一个提案,提出了“凡有重大活动,应在附近增设流动厕所和设置临时路标,以方便有关服务人员”的建议。这个提案当时曾遭一些人善意的嘲笑,认为是区政协委员的水平。但没想到它却受到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,当年就投资26万元,增设厕所。这个提案还被评为当年优秀提案。
资华筠就是这样,在学术上严于律己,并通过自学成才和艰苦研究获得了成就,而生活中的她充满热情,宽以待人,受到人们的尊敬。她的逝世令人悲痛,而她的学术成就和她的品格将永远留在人们心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