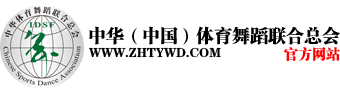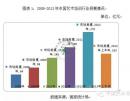一般而言,有故事情节或者眼花缭乱效果的演出相对比较容易接受。然而,现代舞不是用眼睛来“看”懂的,而是要为想象腾出空间,恰如山水画的留白。当灯黑下来,舞台上干干净净的,舞者用一个小时的时间,用身体诉说最隐秘的话,观众则首先需要坐得住,并调动所有的感官手段去填补想象。
林怀民的《松烟》前脚走,沈伟的《声希》后脚来。
《松烟》和《声希》更多是纯粹的意象表达,不同人必然有不同感受。解读的多义,正是现代舞的审美价值所在。
《松烟》不讲故事,只是用舞者的肢体和呼吸去呈现烟无形或有形的状态。男舞者的巨幅黑裙,女舞者晃荡的白裤,形成黑白分明又此消彼长的“场”。天幕投影浮现出瓷器釉面纹理的特写,或纤白脆弱,或釉粒斑斓,时而展开,时而遮蔽,淡入淡出浑然一体。舞蹈从极简的“无”中孕育。追光下身穿白裙的女舞者在静谧中启动,肢体从律动中逐渐获得力量,在行与停、动与静的控制下,另一位静默的舞者开始加入。四下寂寂无声,舞者的转身挪腾,呼吸的韵律节奏,都直达观众的感官。直到突兀的声音进入,带着松烟燃烧时的裂帛声,如同新生命诞生前的撕裂。舞者的缓慢深沉的呼吸吐纳,时而突然发力,疾速舞动、踢打奔跃,顷刻间又恢复了轻柔曼妙,在刚与柔、急与缓、间接与直接、紧张与松弛之间取得了巧妙的平衡。《松烟》的舞者不仅是精准优美的表现,更是一种由内及外的精神修炼,云门的舞者每日不仅要修习打坐、太极,还要练习书法。
沈伟与其说是一位舞蹈家,不如说他是一名视觉艺术家。其舞蹈剧场是开放性的,把东西方的各种生命和文化元素融入其中,并跨越不同艺术形式的界限,从而成为其独有的独特舞台美学特征以及舞蹈语汇。看沈伟的作品,既能明显感觉到中国传统戏曲身体语汇的融入,也能感受到强烈的西方现代舞蹈的特征。中国舞蹈源自古典宫廷舞,脚向内、中心往下沉、讲究内含;西方现代舞从芭蕾发展而来,脚向外、身体呈放射状,想摆脱地心引力。在沈伟看来,现代舞绝不只是个人情感的发泄。他非常重视理性思考在编舞中的作用,“感性入,理性出。个人情感只是初级阶段,把感性认识通过理性思考消化之后,重新表现,得出的观点和认识才具有普遍性。”他在接受采访时说。
《声希》(Folding)的中文名取自老子《道德经》里的“大音希声,大象无形”,舞台以八大山人的游鱼画为背景,音乐配以藏传佛教僧侣的吟诵。舞者面涂白灰,头戴古代仕女的肉色高髻,以红黑两色长裙曳地而行,红与黑强烈对比。其舞蹈肢体语汇的核心正如其英文名字所示的“折叠”,无论是双人舞中两位舞者肢体的交错折叠,还是单人舞中舞者的扭折,均极富东方韵味。另一代表作《春之祭》中,沈伟将斯特拉文斯基的《春之祭》(The Rite of Spring)进行颠覆性改编,方形舞台被纵横的线条切分,面无表情的舞者如同起落的棋子,也如跳跃的音符,试图用最简单的设计和最单纯的方式去与音乐作品进行互动。《春之祭》舞台地面由沈伟亲笔描画,他除了编舞,还身兼舞美设计、服装、化妆、灯光等多重身份。他在演后谈时强调,与其说是舞蹈家,他更愿意说自己是艺术家。
林怀民从内蕴上挖掘传统的精气神,侧重于建构自己的剧场美学体系,从他对舞者“气”的强调中可以感觉其对传统的重视。而沈伟在创作时注重视觉的突破,虽然对中国元素也是顺手拈来为己所用,但重点不在“立”而在“破”。
两位影响力颇大的舞者风格上的差异,或许基于年龄及经历的不同:沈伟自小习国画,湘剧科班出身,参与中国第一个现代舞团的开创,近二十年来生活在纽约;林怀民十几岁开始发表小说,留学回台后开始舞蹈创作,四十年来致力于台湾舞蹈的开创与教育。窃以为,对任何艺术家和作品的评论不该忽视其在历史长河中的个体坐标。在“立”与“破”的现代舞之道中,林怀民和沈伟糅合中西方艺术精粹,可谓殊途同归。